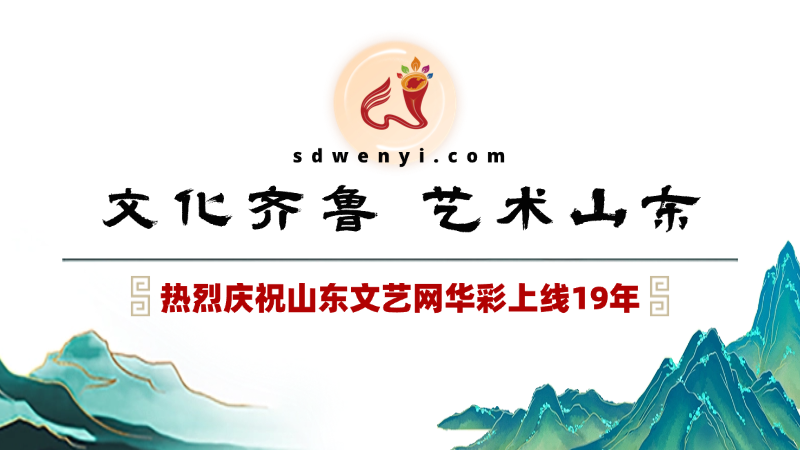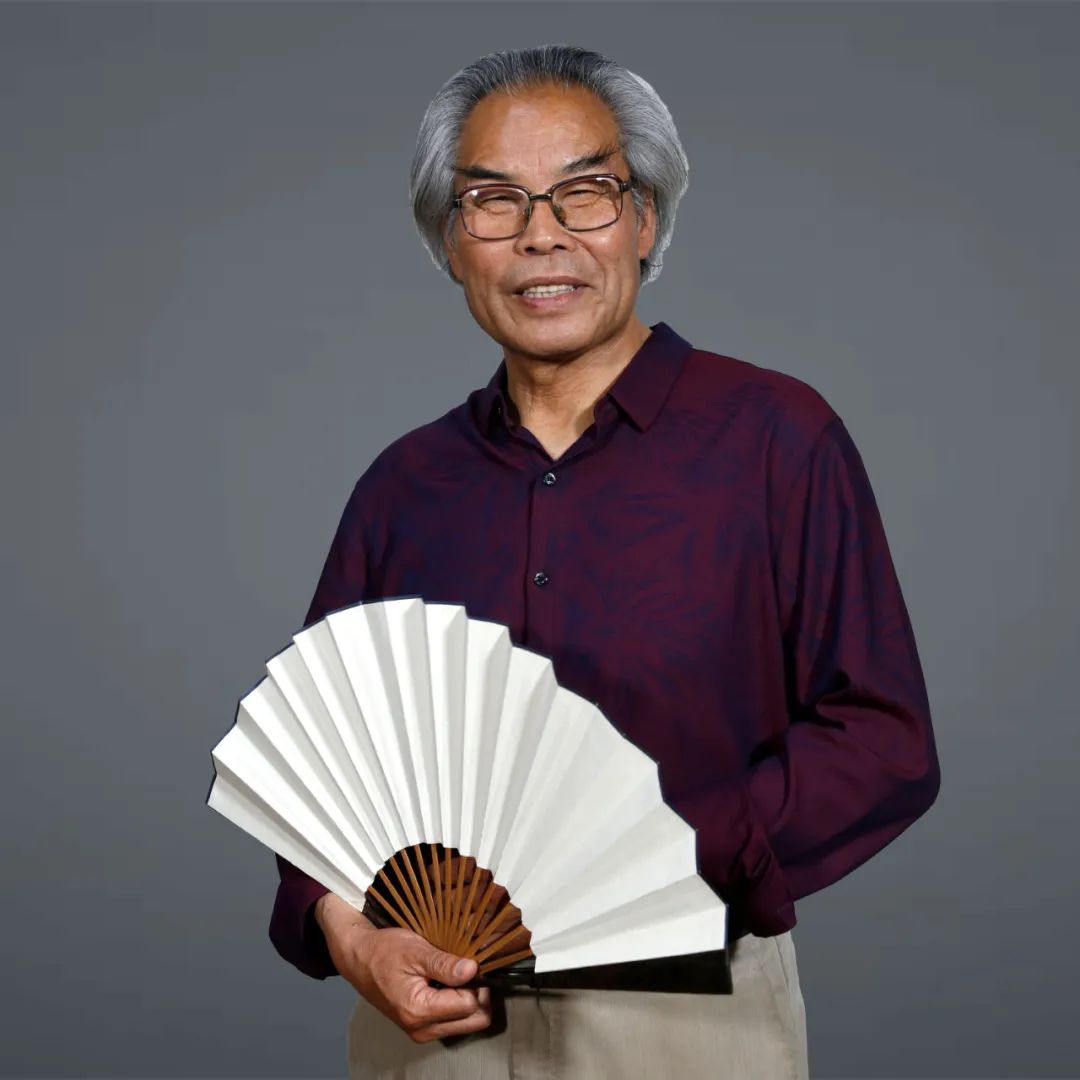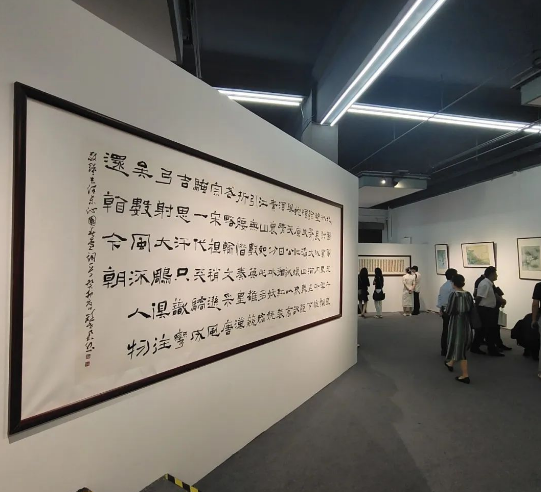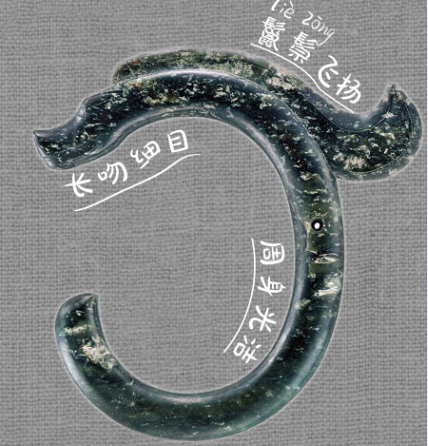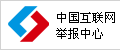山东文艺网> 文学> 浏览文章文学
又一次踏进史铁生的“地坛”
第一次走进地坛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史铁生是谁;第一次接触史铁生的时候,也不知道《我与地坛》与这个人有何关联。初中一年级语文课外读本,开卷第一篇文章至今我还记得,是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从此我认识了这位作家,彼时距离他1991年1月在《上海文学》发表《我与地坛》,刚刚过去一年多。后来渐渐听到身边人提到这篇散文,包括我父亲,大概是因为同姓的缘故,他对这位作家格外关注。我久已记不起第一次捧读这篇文章是什么时候,只记得文章很长让我一时没了兴致,我以前不大喜欢看长的东西,翻几页不见结束就意兴阑珊,每每中辍。
地坛离我家不算很近,大概是我十几岁以后才去过。我家本来紧邻天坛,小时候在天坛里和小伙伴一路追逐玩耍到大,闭着眼也能从公园里的任意角落走回家。而第一次到地坛觉得既小又普通,平平无奇。后来因为在地坛办书市才去得比较频繁,有好几届几乎年年不落。所以地坛留给我的基本印象,就是书市和每年的春节庙会。大概三十几岁以后,我才第一次有机会在平常安静的时刻走进地坛,也终于想正式读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在此之前,我对史铁生的阅读体验大概只有《秋天的怀念》。小说可能零星读过一点但印象不深,因为《秋天的怀念》文章很短,又是上中学读到的第一篇文字,所以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当时包括现在所认为非常漂亮的文字,用极简的篇幅就把一段对母亲的不舍和懊悔表现得真挚感人。后来买了《史铁生作品全编》,第六卷散文随笔,开卷第一篇同样是这篇文章,读来依然感动。《我与地坛》基本是《秋天的怀念》某种意义上的扩写和深化。里面也写了母亲,又不止写母亲;写了怀念,又不全是怀念。这是一篇充满高度哲思的抒情散文,它道出了人类生命的深层意义。
终于有一天,我忘了是第几次走进如今的地坛,手里揣着史铁生的那本书。我从最西边的牌楼往里走,这是明清时期皇帝祭祀时进入地坛的传统路线。经过一段不太长的叫广厚街的小径和一重外坛墙,就到了售票的坛门。史铁生在15年中大概也多次走过这样一段路进入地坛吧,只不过那时的地坛很荒疏和萧索,且不收门票罢了。所以文章里才有了那个每日穿行公园上下班的女工程师。秋天的北京有许多欣赏银杏树的地点,其中就包括地坛。今天人们最喜欢到地坛游览的季节就是秋天,特别是银杏叶由绿转黄至纷纷凋落的时刻,几乎是地坛游人最多的时候。人们或拾起一枚叶子举向天空,或是捧起一大把黄叶向上抛撒,做出各种时尚的打卡姿势拍照留影。中央甬路的古柏下,是一簇簇的鸽子逡巡着寻觅啄食游客撒下的一把把鸽粮。然而,这些手举相机或手机的人在按下快门的一刻,或许难以想到一个作家与这座园子有着宿命般的羁绊。
1969年1月,18岁的史铁生作为清华附中的高才生和另外12位同学来到陕北关家庄插队。史铁生患有先天性脊柱裂,后因遭遇一场大雨发烧感冒,病情加速发展,最终导致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家中,史铁生郁郁不振,便时常独自摇轮椅到地坛来散心。这时他才刚刚21岁。正是人生中最好的年纪,也是史铁生自己“最狂妄的年纪”,却戏剧性地失去了行走的能力。男人在冲突或压力面前往往会习惯性地选择独处以缓解和调整情绪,这在心理学上称为“树洞模式”。而地坛就充当了史铁生的“树洞”。我们应当感谢地坛,使得他拥有了一方独立的安宁,疗愈内心的不平。所以他说“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彼时地坛的荒芜、沉寂与作家的心境形成共振,成为他回避现实又直面内心的最佳去处。因此史铁生摇着轮椅进入地坛就成了一种必然,也是一场命中注定的相遇。
地坛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开辟成市民公园,随后由于战乱和时局动荡疏于管理,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已是满园荆棘、荒草丛生。50年代曾有炮兵学校设在地坛内,园中心的方泽坛被用作二炮仓库,四周布以铁丝网,成为军事重地。进入80年代后军队撤出,公园开始逐渐有序恢复建筑与景观。那时的地坛是人们业余放松散步、锻炼身体和练习气功的场地,所以尽管游人不少,但好在安静清幽。于是成为史铁生的精神避难所,它承载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生命密码。
在地坛的杂草残垣间,史铁生试着用显微镜一般的眼勘察荒芜之下的生机,他有大把的时间来完成这一常人无法胜任的课题。蜜蜂、蚂蚁、瓢虫、蝉蜕,他甚至能看到露水压弯草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听见草木片刻不止窸窸窣窣竞相生长的声息。这是一种入定之后的境界,使他感受到生命的韧性从不由体量衡量,更不因苦难定义。地坛表面颓败清幽而内里则鲜活无比。除了他,地坛里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访客,无论散步的老人、唱歌的青年,还是捕鸟的孩童,他们都普通得无以复加,他们的平凡也在立体地诠释苦难并非某人的专属,活着本身就是常态。地坛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平等地接纳每一个到访者。它作为拥有五百多年风雨的一个老者,见惯了无数渺小个体罹患的劫运变故,但它始终如一地静穆与淡然,亘古不变。
在地坛的杂草残垣间,史铁生多次经历着从“求死”到“求生”的残酷挣扎。那些长时间坐在祭坛下独处的时光中,他反复不停地思考“要不要去死”和“为什么活着”,甚至真的有过出门寻死的冲动。经历过种种生死边缘的徘徊之后,他终于顿悟“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读到这里,忽然发现此时的史铁生和写诗的海子好像具有某种精神共通性,只不过史铁生在一番精神挣扎后选择求生,后者最终走向凄冷的铁轨。史铁生之能舍死向生除了地坛还有他的母亲。母亲是史铁生人生中无法回避的缺憾,在《秋天的怀念》《合欢树》等文中均多次流露过母亲无私的爱与自己曾经的固执倔强的矛盾。已患肝病的母亲心里只牵挂儿子,茫然又急切的脚步和史铁生的车辙一样,十几年来,遍布了地坛每一处角落。原来,活着从来不仅是为自己,更是对爱自己的人的责任。史铁生突然从自我的巨大堡垒里走出来了,他“看得见”母亲了,他甚至能看到母亲夜里因疼痛辗转反侧的画面,母亲的苦,母亲的痛,他也终于都“看见了”。地坛也就成了他缅怀母亲、理解母爱的载体。
在地坛的杂草残垣间,史铁生获得了重生、完整和救赎。双腿瘫痪之后更加令他万般痛苦的是败血症、尿毒症和肾功能障碍等病症接踵而至。离开了陕北牛棚的腥臊,却依然每天都要与尿液为伴,这种种一切都让史铁生觉得耻辱。然而地坛的荒芜接纳了史铁生的痛苦,也治愈了史铁生的精神创伤,更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源泉。后来他许多作品中表露的生死观、苦难观,差不多都能在地坛的经历中找到源头。如果说史铁生是一位智者,地坛就是令他开悟的菩提。史铁生终于打破身体健全才是人生完整的认知,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形式的完美,而在于体验的深度。他最终用写作实现了精神的站立和灵魂的伟岸。
《我与地坛》的精神内涵,使得地坛也从皇家祭坛变为生命课堂,成为后人追寻生命意义的精神地标。曾有人提议在公园中树立史铁生的雕像,后未能实现。不过随着“铁生余华友谊树”的出现,人们似乎用另一种形式在地坛纪念史铁生。公园东北有两棵国槐,一棵上面写着“认养人:余华的朋友铁生”,另一棵写着“认养人:铁生的朋友余华”。两棵树是普通游客认养的,承载着对史铁生的景仰,以及对两位作家深厚友谊的倾慕。走出地坛的史铁生的确乐观开朗了起来,余华曾经回忆:“铁生给我写过一封信,信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他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怨言,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
如今许多青年人走进地坛,在友谊树前拍照打卡,就像每年春天和秋天纷纷走进鲁迅故居的丁香花丛和老舍故居的柿子树下拍照一样。我一度认为《我与地坛》不是为青年准备的,没有经历过生活捶打的年轻人哪里来的那么多困苦和挫折呢?而且如今的地坛着实有些喧嚣了,已不复史铁生徘徊那些年的静好如初,就像当代人无法感知认同木心笔下的《从前慢》一样。中老年群众歌舞和青年打卡拍照成了当今公园里一动一静两大主题。
我怀揣《我与地坛》走出公园南门,迎面即是二环路的车流滚滚,背后是夕阳残照和古柏常青,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昼夜交替、四季轮转莫不是轮回,那么生命确是一场循环与延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人生课题,当代人的焦虑郁结早已渗透日常。今天的地坛虽已不再适合静思冥神,但直面自我、接纳苦难、寻找意义是人们永恒不变的生命命题。
就把“地坛”永久地留给史铁生吧,每个人都应找到属于自己的“地坛”。
下一篇:张旻:碑后面的青海
注:本网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凡本网转载的文章、图片、音频、视频等文件资料,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

扫码关注
山东文艺网公众号

- 11-25小雪 彭连熙图说二十四节气
- 02-09【越调·天净沙】兰贵人茶 朱善
- 02-06兰贵人·茶韵 文/东方美陵
- 02-04饮国香兰茶有感/刘明才
- 02-01茗品兰香吟/刘如彬
- 02-01欣闻兰茶雅会举办启动仪式感赋联
- 02-01咏兰贵人茶/王凌晓
- 01-31迎新春书画联谊暨兰茶雅会文化之
- 01-23在兰陵,该怎么说说这兰 ——
- 01-23兰陵兰/李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