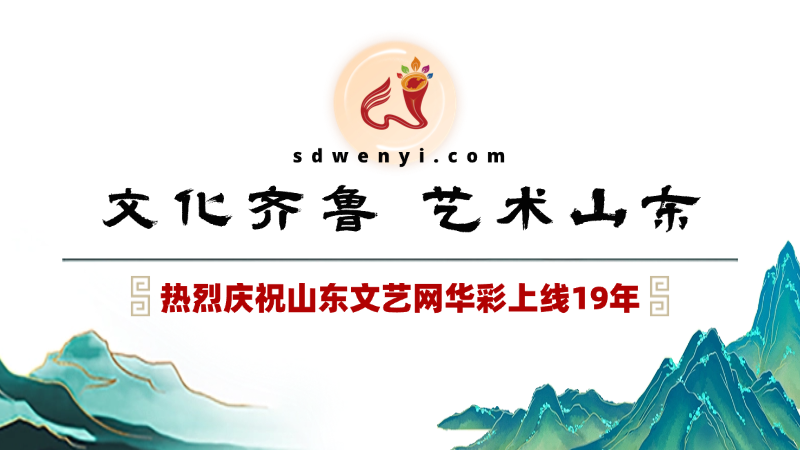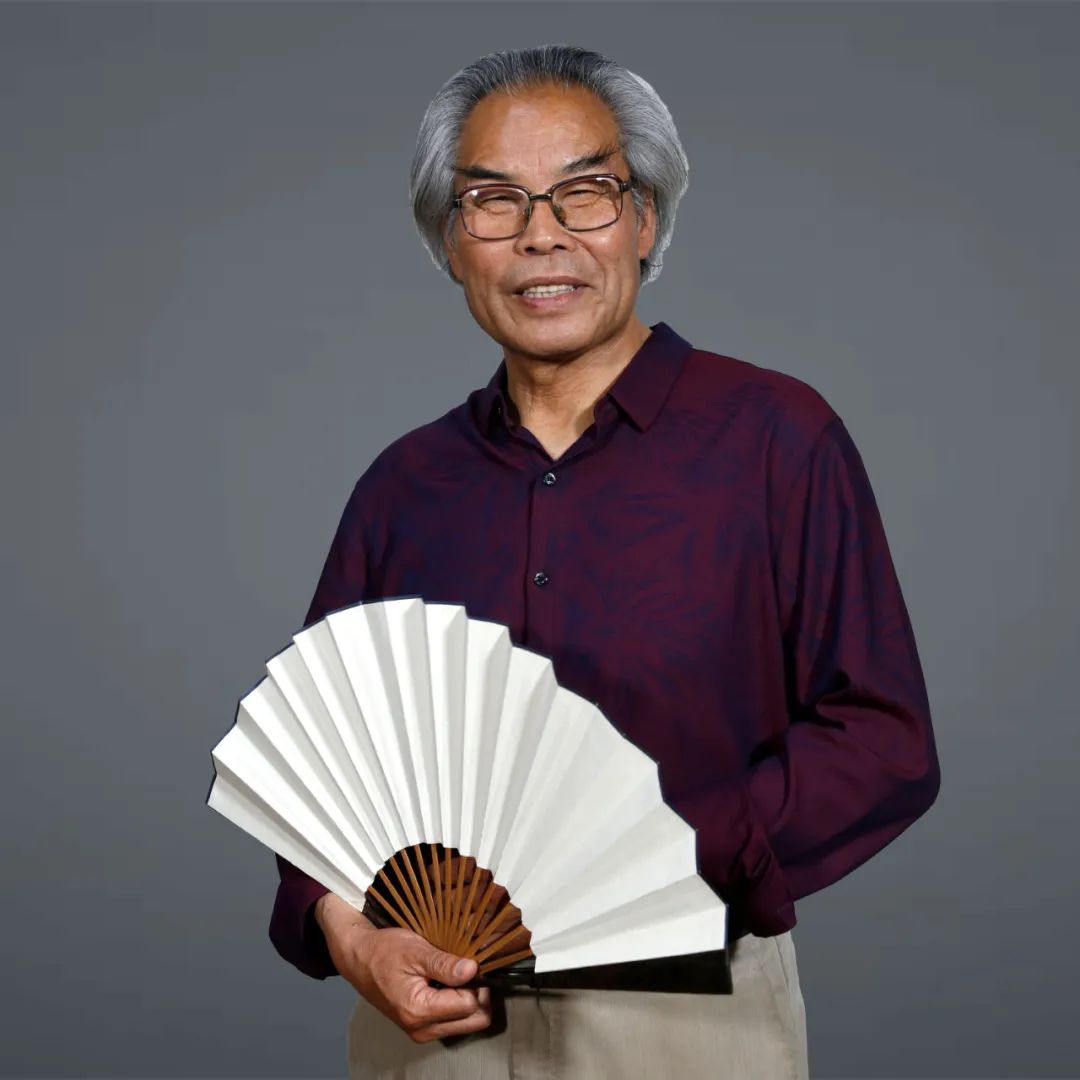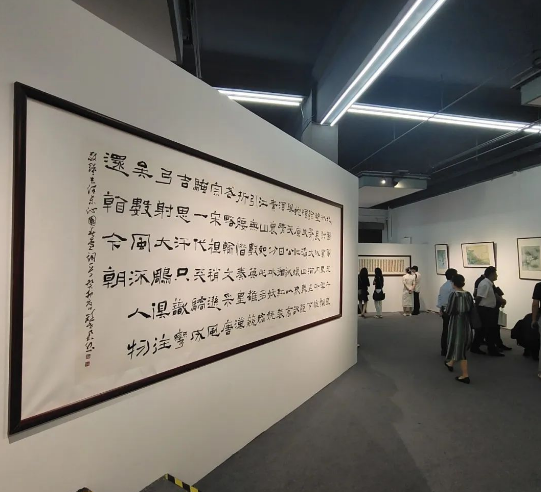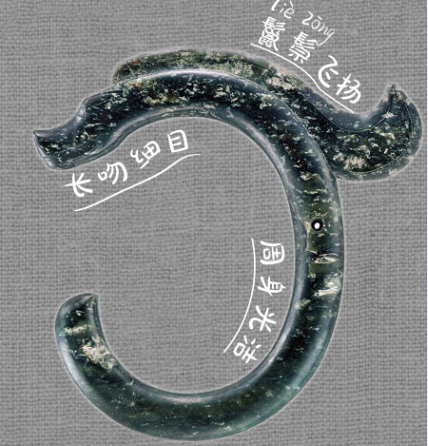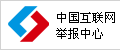山东文艺网> 文学> 浏览文章文学
[图文]知青:烙印于大地的温度
风起,叶落;雨打,檐滴;春浓,花绽;雪落,心澄。人生,本就是一场饱蘸沧桑的跋涉。青春的激流奔涌,中年的溪涧低吟,纵使铅华褪尽,底色深处,依旧沉淀着驳杂而坚韧的光泽。值此落叶低语的深秋,一段被时光掩埋的集体记忆——“知青”——便如星子般悄然浮现。它并非我生命的全部经纬,然蓦然回首,那牵强的笑容里,仍洇染着几许难以言说的苦涩,在岁月的夜空中明灭如萤。
一个特殊的时代,以不容置疑的姿态,为我们这群五零、六零后,烙下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这枚灵魂徽章承载的并非单纯的青春记忆,而是城乡二元结构撕 裂下的生存实验。1955年始,这场运动高擎“消灭三大差别”的理想旗帜,却在实践中演变为解决城市失业的泄洪闸——1966-1968年,全国积压400万毕业生无处升学就业,广袤的农村,无奈地成为了政治经济的双重缓冲带。
它承载着共和国特定历史节点的激流与漩涡。诚如史家所言,知青史,“是一面异常丰富的棱镜,既折射出新中国青年在蹉跎中奋进的身影,也映照着共和国曲折前行的年轮。”当1700万青年被时代浪潮抛入乡土,个体的命运轨迹,便已镌刻成历史唯物论的血肉注脚。
四十五年前那场席卷青春的浪潮,其评价注定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这种分歧本身,正是其历史魅力与复杂性的深刻注脚。历史从未是非黑即白的简笔画,人性的微妙深邃,交织成命运的繁复图景。情感的纠葛、家国命运的交融、青春认同的迷茫、理想奉献的悲壮,其跌宕起伏远超常人想象。我愿以文字为舟,承载着切肤的体悟和对史料的爬梳,以未冷的热情,继续讲述这属于一代人的故事,讲述我那段嵌入大地的崎岖历程。
细细思量,知青群体中个体的感受千差万别,因理想光谱、教育背景、安置方式、环境条件及下乡时机而异,实属常理。然而,若一提及此,便陷入愤懑的“诉苦”与单向度的“声讨”,将持不同见解者斥为“异己”,则难免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知陷阱,失却了历史的宏大与复杂。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时代的车轮将我抛掷于石门东山峰农场。三年的寒暑轮替,让我亲历了知青生活的肌理与骨髓。“极其辛苦”远不足以概括其痛苦的实质。那山区的贫困原始得令人窒息;建场的艰辛超越了生理与精神的极限。十六岁的我,便这样被时代的巨浪裹挟,沉入一片精神的“蛮荒”。
特别是还未成年,却要经受肉体的炼狱:超强度的劳作榨干了少年最后一丝气力,饥饿如影随形,胃囊在“红锅菜”催化下永陷空洞。每餐斤余米的饭食,在缺乏油水的“红锅菜”(萝卜、酸菜、盐水辣椒汤轮番上演)催化下,化为更深的匮乏。紧握冰冷的锄柄,目光总被食堂炊烟牵引,贪婪地捕捉那虚幻的米香。稚嫩的肩膀,过早地扛起与年龄极不相称的重负。这非个别苦难,而是系统性生存危机。1973年李庆霖致信毛泽东泣诉“无米之炊”,折射全国知青日均口粮仅0.4公斤的普遍困境。
冬日尤甚——脚蹬凝结冰疙瘩的硬鞋,在朔风中修路、筑坝、挑石、垒田。皮肉紧贴鞋内寒冰,那钻心的刺痛,至今仍能穿透骨髓的屏障。最惧大雪封山时,深入老林背负柴薪。百多斤的树捆,数米长的原木,压弯了脊梁,在无路的陡坡上喘息、跌撞、攀爬,仿佛下一秒便要被这沉重的荒野吞噬。
而比肌体煎熬更甚的,是精神的苦寒。背负着“家庭出身”的沉重枷锁,“黑五类”子女的标签如影随形,入团、入党、参军,皆是遥不可及的幻梦。无形的歧视如空气般弥漫,灵魂深处,压着沉甸甸的巨石,令人窒息。当种种苦难如潮水般涌来,绝望便如冰冷的藤蔓,缠绕收紧——难道一生就此锁闭在这荒寒之地?青春的烈焰骤然坠入幽谷。彼时,真正噬咬人心的,非仅劳累与贫瘠,更是那无边无际的空茫感,是生命价值被连根拔起的虚无。“生存还是毁灭?”的拷问无声回响。我只能将一颗心细细揉碎,揉进无边的寂静,揉成一片沉重的沉默。
然而,终究未曾沉沦。这源于一丝不肯熄灭的微光:不自设绝境。在希望渺茫之际,我唯有以数倍于常人的劳作,试图洗刷那无形的“出身原罪”。更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贪婪地啃噬书本,用知识缝补破碎的天空,为灵魂凿开一隙透光的孔洞;小心翼翼地处理周遭关系,在磕磕绊绊中,竟也走完了这三年崎岖路。
平心而论,农场领导与职工对知青,确存一份朴素的关照之心。在政策允许的狭缝处,对表现优异者,“出身”并非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少知青得以擢升至管理层——场党委、分场书记、队长,乃至会计、统计、医生、教员、机手等。我亦因勤勉,偶获信任之光:出席农场首届先进知青代表大会,担任排干,负责修水库的劳力调度,甚至被推荐去卫校、学开拖拉机。这些微光,至今思之,仍能感到一丝暖意,让我确信,即使在最冰冷的岁月褶皱里,人性的“温度”依然顽强地存在着。
若据此便论断上山下乡运动于知青全然积极,则悖离我本意。我仅忠实记录亲身所历,非标榜崇高,只是灵魂深处的诚实回响。当下回望知青岁月,调子常是灰暗、悲怆的;亦有人视其为不可磨灭的明丽画卷,斑斓世界。而我深知,那是一个五味杂陈的熔炉,诚如狄更斯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我由衷羡慕那些能入团入党、进入场部机关的“幸运儿”。伏案行文、作报告,书报相伴,偶有劳作,三餐飘着油荤——他们是“时代的宠儿”,是我心中最“崇高”的彼岸。然,个中滋味,谁人尽知?唯大浪淘沙,方显真金。如今知青聚首,步入迟暮的我们谈及下乡带给国家与个体的创痛,往往直言不讳,贬多褒少,这或许是多数人经历的真实回响。但亦不可否认,亦有人深情追忆那段岁月赋予的深沉、坚韧与练达——“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遇事不再冲动偏激,更加珍爱脚下土地,拥抱晚晴。
对知青的历史定论,终将铭刻于一代人以血肉之躯、以滚烫青春,在共和国艰难岁月里书写的慷慨悲歌。我们——与共和国同频共振的一代人——曾以稚嫩双肩,支撑起危厦的基石,承受了远超年龄的坎坷与磨砺。谁说我们“垮掉”?共和国的土壤,浸润着我们青春的汗水;谁说青春已逝?共和国的旗帜上,永远飞扬着我们那代人以特殊方式淬炼出的风骨。
纵有“流产之说”萦绕,许多知青并未疏离时代,而是以更沉静、更复杂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的变革与转型。审视历史,断不可囿于个人恩怨得失。唯有跳出个体局限的“井底”,超越片段经历的碎片,立于国家全局与历史长河之岸,方能洞见事物真谛。正如史学家钱穆所强调的,需抱有“温情与敬意”。
改革开放三十余载,其伟力在于“人”的觉醒与解放——“以人为本”成为时代强音。这翻天覆地的变迁,我们亲历亲证,个体命运与国家宏大叙事,早已血肉相连。若仅因个人曾历数年苦楚,或一时委屈,便以偏概全,断言知青历史优劣,未免失之浅薄与狭隘。
客观评价知青历史,其“核心”必归于“人”——人的命运沉浮,人性的复杂光谱。回望整段知青历程,其独特的“温度”,正蕴藏于这复杂人性的褶皱里,在严酷环境中闪现的人性微光、互助温情、以及逆境求生的坚韧之中。以大历史的悲悯目光穿透尘烟,打捞那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体命运,勾勒历史脉络下隐秘的生存轨迹,拾捡政治化叙事中遗落的灵魂碎片——诚如评论家所言,这便是一部“有温度感的知青历史”。它超越了简单的功过评判,直指生命在特殊境遇下的存在状态与精神韧性。
再忆农场琐事,那些极具时代荒诞色彩的“惊世骇俗”之举——男知青们“老道”地扫荡菜园(如秋风卷落叶般掠尽辣椒),以枕套为囊“巧取”家禽,邻近市镇商店失窃、市场纷争,多系农场青年“杰作”,斗殴亦常惊动保卫与公安。乡民们面对此等“罄竹难书”,虽瞠目结舌,手足无措,却并未“落井下石”,反报以惊人的宽宥与理解。
这种“时代的宽余”,亦是那段冰冷岁月里一抹难以忽视的暖色,是人情在高压下的朴素坚守。四十年烟云散尽,那些闹剧般的故事,终随知青返城化作苦涩的诙谐。凡亲历者皆知:那是人生一段浓重的无味、艰辛、失落与沮丧。但真正淬炼入骨的,却是劫波渡尽后的成熟与对世事的通达。萨特说:“人是自己行动的总和。”这段经历,无疑是我们生命总和中沉重而独特的一章。
无论如何,知青“上山下乡”,纵有彼时政治经济的多重推力,其根本仍悖逆了社会进步的潮流与绝大多数青年求学择业的天然意愿。他们大多未及成年,学业未竟,便无端卷入政治洪流。在阶级斗争的严苛语境下,许多背负父辈政治“原罪”的知青,被打上异类烙印,参军、招工、升学之路尽断。即便同为下乡者,命运亦判若云泥。及至政策松动,返城、读书、参军,更成“八仙过海”的竞技场,“表现”常不敌“出身”与“关系”的冰冷现实。下乡时或同乘一列车,返城路却各历辛酸,布满荆棘,深刻映照了时代的不公与个体命运的悬殊。
但不管怎么说;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坐标和人性探照灯下进行审视,“知青”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理应成为一部更具深度、温度和普世价值的“生命史诗”。
广阔的农村天地,我们曾深深踏入。脚下是温暖的土地,亦是沉重的沧凉与莫名的自在。跋涉过的山径,弥漫着扑朔迷离的知青气息——酸涩交织,苦中回甘。这段经历,它慷慨赠予(坚韧、务实、对底层的认知),也无情剥夺(学业、青春的正常轨迹、部分人的前途);赐予片刻融入自然的欢愉与同袍情谊,也留下长久的精神阵痛与身份困惑。其玄妙在于,看似不动声色的时光流转,却将每个人的命运雕琢得千差万别。然而,若仅以“牺牲品”定义一代知青,实属片面不公。无论当年抑或今朝,知青都为共和国早期的建设(尤其是在艰苦地区的拓荒)、为弥合城乡文化鸿沟(尽管方式特殊且代价巨大)、为改革开放的伟业(积累了丰富基层经验,成为各行业骨干),倾注了不可磨灭的心血与汗水。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曾真实地接纳和磨砺了我们。
方寸之地,回旋着跌宕的人生;朴素的生存哲学,在扑朔迷离的命运中闪烁微光。知青的历史涛声渐远,一丝惆怅悄然划过心湖。我知晓,那如火如荼的青春,早已定格为过往的风景。我不愿沉溺于历史的怅惘,迷失于感伤的暮年。亦深知,关于知青的喧嚣,已无需更多。唯愿我们永不轻慢自己的时代,用心谛听时代奔涌的正声,而非沉湎于喑哑的负累。“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综此,我仍坚持:上山下乡运动,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整体上的负效益及其对一代人造成的深重影响不容轻忽。然而,纵使当年历尽艰辛,汗泪交织,我依然深深怀念那片承载了我青春热血的东山峰土地——怀念那云雾缭绕的朦胧山色,怀念茅草坡上寂静的风吟,怀念层峦叠嶂的壮阔胸襟,更怀念那里纯朴的山民、善待我们的农场职工与基层干部。这份怀念,并非对运动的肯定,而是对那片土地、那段青春、那些共同经历磨难的人,以及自身在绝境中未曾熄灭的生命之火的深切眷恋。这份眷恋,便是**烙印于大地的温度**,是生命在荒寒中自发生长出的暖意。
时移世易,当年的少男少女,今已鬓染秋霜,步入古稀。回望那段历史,纵使坎坷遍布,命运多舛,然而,一代人的青春淬炼,一代人的悲欣交集,一代人的激越与沉潜,一代人的失落与求索,历经四十五载光阴的沉淀与过滤,终酿成一坛浓烈而醇厚的集体情结,一丝穿越漫长岁月、隽永深长的生命眷恋。它已融入我们的血脉,成为解读这个国家与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密码。
下一篇:[图文]茶与酒
注:本网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凡本网转载的文章、图片、音频、视频等文件资料,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

扫码关注
山东文艺网公众号

- 11-25小雪 彭连熙图说二十四节气
- 02-09【越调·天净沙】兰贵人茶 朱善
- 02-06兰贵人·茶韵 文/东方美陵
- 02-04饮国香兰茶有感/刘明才
- 02-01茗品兰香吟/刘如彬
- 02-01欣闻兰茶雅会举办启动仪式感赋联
- 02-01咏兰贵人茶/王凌晓
- 01-31迎新春书画联谊暨兰茶雅会文化之
- 01-23在兰陵,该怎么说说这兰 ——
- 01-23兰陵兰/李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