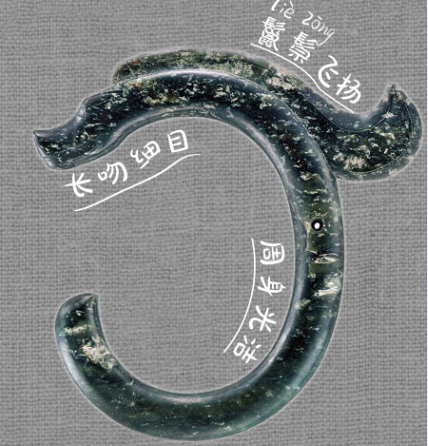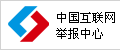山东文艺网> 文学> 浏览文章文学
清代乾隆时期诗学的新发现与再认识
张宇超
清代诗学文献数量庞大,体例繁复,这是其远过于前代诗学的两个最突出的特征。民国时丁福保开始汇编整理首编《清诗话》,收书43种;上世纪八十年代郭绍虞先生的《清诗话续编》,收录34种;本世纪张寅彭教授又辑《清诗话三编》,收入95种。三书共收诗话174种,有清一代之诗学精华,大致得以呈现。2012年,张寅彭教授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开始编辑《清诗话全编》(以下简称《全编》)这一特大型丛书,成立点校团队,进入了全面整理清代诗学文献的新阶段。“诗话”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形式。[1]清代诗学文献不仅仅包括诗话,更有诗评、诗法、论诗诗、摘句图、点将录等多种形式。丁福保编《清诗话》即用“诗话”泛而言之,《全编》亦沿用这种做法,虽名“诗话”,其实乃一并收录清代诗学各种体例之“勒为专书”者。又以“自撰”与“汇辑”为标准,分成内、外两编,内编按清代十帝次第,划分为顺康雍、乾隆、嘉庆、道光、咸同、光宣等六期,外编按题旨内容分为断代、地域、诗法三大类。[2]顺康雍期收书89种,201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先期出版。202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推出乾隆期,共收书103种,其中包括《清诗话》已收11种,《清诗话续编》已收10种,《清诗话三编》已收17种,新增之作达65种。乾隆期也按成书先后次序,以叶之溶《小石林文外》为开端,吴询《画溪论诗》为最后一种。既有常见的《带经堂诗话》、《随园诗话》、《雨村诗话》,也有稀见的《鸿爪录》、《范金诗话》、《忆旧游诗话》、《此木轩论诗汇编》等书。在突出《全编》之“全”的同时,又讲究别裁,将历来书目著录的《槐堂诗话》等书剔除,列入“存目”,并将《古今诗麈》等移入外编。近500万字的文献点校工作,主要由上海大学文學院副教授刘奕一力承担,整理质量堪称精当。如此大批量的按照现代学术标准整理的诗学文献的整体推出,对于全面深入开展乾隆时期的诗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值得详加评介。本文拟从选目、版本与提要三个方面,对其价值作一简要述评。
一、选目之精审
确定乾隆期诗话收录的书目,这是第一步要进行的工作。《全编》所收诗话以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为主,参以蒋寅先生《清诗话考》。就乾隆期的选目确定而言,具体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一)考订成书时间
由于《全编》按成书的先后次序排列,首先需要考定所收各书的成书时间,结果颇有与此前各家书目著录不相一致的情况,既有原为乾隆期者而遭剔除,亦有原为其他时期者而被纳入。前者如袁若愚《学诗初例》,此前学界皆据乾隆二年(1737)刊本,收入乾隆期中。此次因为在西南大学图书馆新发现有康熙五十四年(1715)刊本,始知乾隆本实为翻刻本,故此书改入《全编》康熙期。后者如蔡家琬《陶门诗话》,卷末自识云成书于道光元年辛巳(1821)[3],乃蔡氏晚年之作。由于新发现浙江图书馆藏有蔡氏早年的《诗原》一书,此本有乾隆五十七年(1792)序,因此根据《全编·凡例》“一人有一种以上著作者,按最早之一种排列,其余接排于下”的原则[4],《陶门诗话》提前收入乾隆期。类似情况尚有若干种,最典型的莫如翁方纲,他的《渔洋杜诗话》成书甚早,其他五种接排于后,以至于他的位置,反列在年辈较他稍大的袁枚之前。这种以书为主兼及作者的编排原则,大抵还原了乾隆时期诗学次第发生的实际过程。
依据成书时间排序,但也有少数成书时间不明者,又需尽量考索其他因素,以酌情确定其位置。如黄任《消夏录》,虽著录有乾隆三年(1738)初刊本,但据今存乾隆四十年(1775)刊本之余文仪序,此本才是初刻本,黄氏生前并未付梓。黄任卒于乾隆十三年(1748),故编纂者不采乾隆三年初刻疑似之说,转据其卒年排列,列在成书于乾隆十五年的纪昀《玉溪生诗说》前。又如马鲁《南苑一知集》有论诗二卷,写作时间无法确知,便以其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举的时间为据,置于乾隆二、三十年间。全期一百馀种,都尽力做到排列有据。这也就是《全编·凡例》强调的“编年”法,是最为朴素、可靠的传统之法。《全编》其他各期也采用此法,读者和研究者如果从头顺次读下来,一部乾隆诗学史、乃至有清一代诗学史的渐次生成展开,便如在目前和了然于胸了。
(二)考订内容
考定成书时间以确定其是否合乎乾隆期的“身份”,另有一个更为基础的“资格”审查,是各书内容的真伪精粗。如南京图书馆有何元锡旧藏钱塘姚石愚节录《槐堂诗话》,各种书目根据字号“槐堂”,定为乾隆时著名诗人汪沆所著。此次整理,发现该书全部抄自宋长白《柳亭诗话》,而且抄得漫无体例,故不予收入,黜入存目。又如方起英辑、张希杰增订之《古今诗麈》,篇幅巨大,仅有乾隆十四年(1749)稿本,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后由台湾广文书局收入《古今诗话续编》,影印出版,堪称难得之书。但复核下来,实际上抄自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全编》以其抄得还算有所旨意遂据其汇辑的性质,移入“外编”的“诗法类”中。[5]这种抄袭他书的现象在清代诗学文献中经常出现,极具隐蔽性,应该小心甄别考辨。[6]
其次,摘取节录他书者,原则上亦应当剔除,以避免重复。如王士禛、袁枚等诗学大家,乾隆朝诗话中多有节录、摘抄者。如王廷铨辑《诗法正宗》、张宗柟辑《诗答问》等书,均取自王渔洋及张笃庆、张实居的《诗问》一书。《诗问》刊刻最早的康熙本已收入《全编》康熙期,故上述诸书不再收录。袁枚《随园诗话》卷帙浩繁,时人多有删繁摘要之举。[7]如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梁同书《随园诗话摘钞》,书法虽精美,显然也不在收辑之列。
再次,两书题旨、内容同一者,往往需要比较优劣、判定关系来确定或存或汰。如山东省图书馆藏安浚德辑《渔洋诗话拾唾》稿本,按诗体分类汇集王士禛著述中的论诗之语,大不如张宗柟所辑的《带经堂诗话》,故收张书而不收安书。又如南通市图书馆藏钱思敏、白璧、钱国琛合辑的《增订诗法》四卷,乾隆三十四年(1769)古琅金石社刊本,乃是增订顺治间叶弘勋《诗法初津》三卷而成。名义上是“增订”,实际上篇幅反较叶氏原书减少,改订文字也较为草率,绝无发明,不及叶氏《初津》远甚,因此《全编》顺治期收入《初津》,而乾隆期不收《增订》,正是选目去取严谨得当的一例。
第四,逐一审慎区分诗话与选本、笔记等书的界限,最是确定收辑与否的难点和用力之处。如纪昀《玉溪生诗说》上卷选诗160余首,虽有解说,而颇似李商隐诗选本,下卷却又为不选的360余首逐一说明理由,而并不录出诗作,则又是标准的诗评体,因而不容不收录。[8]而如王元启《读韩记疑》十卷首一卷,嘉庆五年(1800)刊本,虽有被著录入诗文评类者,其实为韩愈诗的选本,所以不予收录。再如翁方纲的《杜诗附记》夏勤邦钞本删去诗作,合乎诗评体例,而台湾师范大学藏有的翁氏杜诗批本,却未脱别集形式,故一收一不收。此类选本与诗评的甄别,《全编》各期所在都有,是一次必要而有益的实践。
(三)有名无实之书
各家书目中著录的清人诗话,有不少并无其书。如安浚德辑《渔洋诗话》一卷,著录为“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此次经编纂者实地查访,实际上并不存在,可能是当时著录时,与安氏的《渔洋诗话拾唾》相混淆。再如廖景文的《古檀诗话》,著录有“南京图书馆藏钞本”,实是他的《罨画楼诗话》、《盥花轩诗话》的别称,也无其书。廖景文另有《小青遗真记》传奇一种,藏国家图书馆,后附《诗话》数则,乃是从《墨稼丛谈》、《羡行偶笔》、《竹屏涉笔》、《峭厓杂录》等书中摘录的关于《遗真记》的评论,其中也有几则署“古檀诗话”,以示廖氏所撰,也并非表示有《古檀诗话》这一本书。[9]
总之,经过内容实勘,乾隆期也一如既往,继顺治、康熙、雍正期后,又一次将历来书目之名录准确化,变得可信、可用。
二、版本之良善
《全编》乾隆期入选的每一种,版本的选择自然也极为讲究,尽力选取善本,作为点校工作底本。这一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选择善本,替换通行本
诗学文献,最为流行的是丁福保的《清诗话》与郭绍虞的《清诗话续编》,其中尤以丁书流行最广。但该丛书使用的底本大多不善,《全编》基本予以替换。如黄子云《野鸿诗的》,《清诗话》所据为《昭代丛书》本,“一曰诗言志”一则,缺最末之“方今圣人御世”一段,而乾隆初自刊《长吟阁诗集》本最早且最全,因此以乾隆自刊本替代《昭代丛书》本。再如查为仁《莲坡诗话》三卷,载乾隆八年(1743)刊《蔗塘外集》,而《清诗话》据《昭代丛书》本合并为一卷,并对原书条目多有删削,又删去杭世骏序。《全编》即改用《蔗塘外集》本,成为第一个恢复《莲坡诗话》原貌的整理本。又如翁方纲《小石帆亭著录》六卷,《清诗话》将前五卷各自独立,而未收第六卷《渔洋先生书目》,此卷定渔洋著述四十二种,是翁方纲极具用心之作,《全编》即补录此一卷,恢复了六卷全帙。
郭绍虞先生编《清诗话续编》,未标明所据底本出处,《全编》在编纂时重新调查确定,并对郭书有所调整补益。如杨际昌《国朝诗话》,郭书所据实为乾隆二十四年(1759)似园刊《澹宁斋集》本,乃最善本,《全编》即以浙江图书馆藏本为底本校核,转据该本收入。又如方世举《兰丛诗话》一卷,郭书实据乾隆间刊《春及堂诗钞》所附者,《全编》据安徽省图书馆藏乾隆刻本校核,并参考了同馆所藏抄本,也并非直接收录《续编》本了事。
名家、大家之作流传广,版本多,版本的选择更需要用心考究。如张宗柟《带经堂诗话》以汇集渔洋诗学的集大成之作,向来为人熟知,人民文学出版社戴鸿森点校本据同治十二年(1873)广州藏修堂重刻本整理,最为通行。据校点后记称,整理时曾删去渔洋语意相同而措辞不同的条目,以及张宗柟的部分附注、夹注。[10]张宗柟“附识”向被清人张宗泰、李慈铭等推重,可以加深对渔洋诗学的理解,故不宜轻加删削。[11]《全编》则据乾隆初刻本,保存了全部文字,完整地呈现了《带经堂诗话》的原始面貌。再如袁枚《随园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反复刊刻,确定其底本的工作十分困难。据郑幸考证,现存清刻本多达三十余种,分家刻本与坊间刻本两大系统。家刻本多有袁枚本人历年的多次增订,可见内容逐年成型的过程,故正编、补遗初刻虽分别始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十七年(1792),但后印之本记事直至嘉庆二年(1797)逝世之年,当出自其最后增补之举,而其他翻刻本的文字差异则不足为凭。[12]因此,《全编》以乾隆五十五年、五十七年小仓山房家刻增修本为底本,底本原阙补遗卷六最后四则,及补遗卷八至卷十,则据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本补足;卷九末二十七则,另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乾隆本补足,形成了一个既可靠又完备的最善本。
(二)稀见本与稿抄本
有些诗话虽有刻本,但传世极尠,向来罕见。如谢鸣盛《范金诗话》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刊本,仅见江西省图书馆有馆藏著录。又如冯一鹏《忆旧游诗话》有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黄裳先生曾有收藏[13],但今不可见,惟台湾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册。《全编》分别与当地学者合作,先录入文本,再悉心校核,使向来罕覯的二书得以重见天日。
相对于稀见的刻本而言,稿本、抄本更为罕见。清代诗学文献中的稿抄本保存至今者甚夥,大多具有唯一性。如周大枢《鸿爪录》六卷首一卷,收于会稽徐氏初学堂《群书辑录》丛书中。该丛书为抄本,仅存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现已扫描成图片,只能通过电脑查阅,整理难度较大。再如上海图书馆藏徐逵照辑《此木轩论诗汇编》八卷,亦系抄本,仅此一部,篇幅较大,辨识整理也十分不易。而沈钟《梦余诗话》二卷,有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毗陵沈氏杂著》清钞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底稿本两种,《全编》得以台湾本为底本,参校中科院本,如其中“冷玉娟”一则原脱,即据中科院藏本补全。此类稿本、抄本往往字迹潦草,书写零乱,辨识度低,整理者需格外投入精力,方能完稿毕功。
(三)域外藏本
在彻底调查、搜集国内各地庋藏的清代诗学文献之外,海外所藏自然也在所不遗,《全编》顺康雍期所收之魏裔介《兼济堂诗话》,即得自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馆。此次乾隆期收入的邵履嘉《耘砚山房诗话》,也是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藏本。邵书乃抄本,此前各种书目未见著录,此次得以首度标点整理面世。
要之,《全编》乾隆期所收各书,版本皆择善而从,从根本上保证了此套丛书的学术价值。
三、提要之精湛明通
《全编》乾隆期每种诗话之前,一如既往,都有张寅彭教授撰写的提要,考订作者生平、版本异同之外,更以勾稽内容、揭示诗学观点为重心,充分展现了张教授数十年浸淫清代诗学的精湛功力与明通见识。考订方面的发现,如《此木轩论诗汇编》作者焦袁熹生卒年有1661年至1736年及1660年至1735年两说,后说实出《清史列传》卷六七,提要据张廷玉撰墓志铭定为前说。再如《莲坡诗话》三卷所据乾隆八年刊《蔗塘外集》,实有先印后印之别。提要指出《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少末两则[14],似为先印本,颇为罕见,便于读者进一步研究。
最值得重视的是论述乾隆诗学方面的内容,提要借助评介每一部著述的机会,具体谈到了乾隆时期诗学的诸多大小问题。如翁方纲《石洲诗话》的提要达两千余字,指明覃溪诗学从渔洋入,又从渔洋出的实质,揭示覃溪如何转“神韵”为“肌理”的形迹。又独具只眼地指出,其说与稍后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质实”的命题,实际上殊途同归,可当一篇简明扼要的清代前中期诗学史。又如这一时期袁枚的“性灵”说一般都耳熟能详,但谢鸣盛《范金诗话》论及吴乔、赵执信的“诗中有人”说,“诗之中还须有我在”,“我有我之性情、我之学识、我之登览吟眺”。[15]改“人”作“我”,成为“诗中有我”。提要指出,这一字之易,正与“性灵”同调,可以窥见乾隆盛世之下个体意识复萌的新气象。当时诗话中虽然盛行此种自我表现意识,如吴镇《松花庵诗话》也有“今人作古诗,不患不古,而患不今,极今而自古”云云,[16]但都不如谢氏这一“我”字表述正式。其后嘉、道诗话中“有我”之说便大行其道了。[17]
王渔洋诗学的走向,也是乾隆时期诗学的一个重要话题。一般认为渔洋诗学在乾嘉以后便“不闻继响”[18],但从《全编》来看,涉及渔洋诗学的材料可以说俯拾皆是,提要多留意予以指出。评论渔洋最充分的自然是翁方纲,他的所有诗学文字,几乎处处都有渔洋的影子。其他人或褒或贬,往往两极。如焦袁熹《此木轩论诗汇编》大贬《渔洋精华录》,逐一点评,半数被斥为“扯淡”[19],如此全盘“恶评”渔洋诗,尚属罕见。[20]崔迈《尚友堂说诗》、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乔亿《杜诗义法》、朱宗大《杜诗识小》等,或对渔洋诗,或对其诗学,都表示不满。但与贬斥相对,乾隆时期还存在着大量渔洋诗学的支持拥护者。提要指出田同之《西圃诗说》虽然标举乃祖田雯之说,但实际上通篇主微妙蕴蓄,重唐轻宋,又由宗唐而对明诗表恕词,引七子王世贞等为同调,这些看法都偏于渔洋诗学一路,而与山姜诗学稍有差别。杨际昌《国朝诗话》以王渔洋为一代宗匠,盛世承平日久,诗风由变趋正,故以“正宗”、“大方”作为录诗的宗旨,多录体制和雅、描写太平风俗之作。雷国楫《龙山诗话》颇不以吴乔攻击渔洋为然,而能识渔洋诗学之精微。更有甚者,郭兆麒《梅崖诗话》为渔洋辩护,乃至摘取赵执信《并门集》中一二诗句,以为同样是“无人”之作。[21]而这些大都成为了乾隆诗学的正面建树。
提要注重揭示每部诗话的特点,勾稽其内容,往往在不经意间凸显出了各家诗话的地域特色,关系到地方诗学的建设。如蔡显《红蕉诗话》记载松江当时学诗者率宗李义山,可补诗史。陈梓《定泉诗话》多论浙人浙诗,其中摘句颇以宋、元人诗及近人诗之咏生活者为主。雷国楫《龙山诗话》记乾隆间吴地诸县诗人甚详,录诗多可观,实为承平时期富庶地区人文之写照。汤大奎《炙砚琐谈》概括各地诗风,有所谓“关中雄、燕赵快、齐鲁骏、河内闳、楚茂、蜀严、晋确、江西冽、浙赡、吴和”的说法。其他如吴镇《松花庵诗话》多表彰秦地之能诗者,伍宇澄《饮渌轩随笔》多记阳湖地区诗人等。而周春以寿长,他的《耄余诗话》所记六十年间诗事掌故,细致详备,多关乎乾嘉间主流人物,又不限于一地。
乾隆期诗话体量最大之作无疑是袁枚的《随园诗话》,提要着重指出了它的这一形式意义,即改变了从欧阳修《六一诗话》到王士禛《渔洋诗话》以自我为中心的传统写作模式,以数倍乃至数十倍的篇幅,全方位地展示出乾隆盛世各地普通百姓的日常“诗生活”。李调元模仿随园,他的《雨村诗话》,也以十六卷补遗四卷的篇幅,广泛记载了他所亲历的乾隆诗坛的实景。廖景文的《罨画楼诗话》、《盥花轩诗话》皆属同类性质。他有意模仿袁枚,兴建园林,晚岁也好远游,都是太平盛世文人的娱乐消遣方法。乾隆时期长篇诗话的产生,与盛世新的生活方式是相辅相成的因果关系,诗话竟然回归了“采风”的功能。
四、结语
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工作,头绪纷繁,难免存在各种艰辛与遗憾,最困难的可能就是原始文献材料的搜寻与采集。就《全编》乾隆期而言,就有几种已知存世与具体馆藏信息的诗话之作,未能寓目而未予收录。如黄立世《柱山诗话》一卷、(山东省博物馆藏清钞本辨蟫居高氏写本《齐鲁遗书》卷十八收录)王煜《渔洋诗话汇编》十六卷。(山东省博物馆藏稿本)前书石玲教授在论述高密诗派时曾予征引[22],后书则有蒋寅教授《清诗话考》提要介绍,谓其“似随读随抄”性质[23]。确切知道馆藏信息却无法浏览阅读,这也是当下古籍整理面对的普遍性问题。笔者对此虽然充分理解,但也希望并相信随着学术生态的日趋优化,定能得以改观。西方文化微观史学家主张通过历史资料的重新挖掘与整理,运用大量细节的描述,从而分析重建微观化的个人、家族或社群,发现精英与大众在历史中的相互关系。[24]《全编》乾隆期集中提供了直接记载乾隆时期社会、文化、文学等现象的大量第一手新材料,可供读者对乾隆时期诗学进行微观化的分析,可以触摸到具有多种样相形态的乾隆诗坛实景。而在注重细节的同时,又需要防止导致“碎片化”的倾向,故西方史学界近年又有反对短期主义,提倡长时段的整体性审视[25]。在乾隆诗学中,王渔洋的接受问题正是这样一条长时段的主线脉,可供我们具体观察和把握清代诗学的走向。其他如对七言古体、七言律诗等文体形式的深入探讨,也是唐后诗学持续实践和探索的对象,而在乾隆期诗话中在在可见,达到了普遍成熟的程度。相信《全编》这一时期的出版,一定能促成乾隆诗学的再发现,达成新的认识。
注释: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中后期渔洋诗学的接受研究”(18CZW028)阶段性成果。
[1]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40页。
[2][4][5][8]张寅彭《清诗话全编•凡例》,《清诗话全编•乾隆期》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2、4、3页。[
3]蔡家琬《陶门诗话》,《清诗话全编•乾隆期》第十二册,第6830页。
[6]如宋顾乐《梦晓楼随笔》实乃摘录王士禛《带经堂集》中部分内容编选而成。参见张东艳《清代诗话<梦晓楼随笔>作者与著作权考》,载《中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94—99页。
[7]如嘉庆间袁洁云:“余嫌《随园诗话》太冗,曾为去其芜杂,存其精华,另成一帙。”袁洁《蠡庄诗话•序》,张寅彭辑《清诗话三编》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591页。
[9]孙爱霞编《清代诗学文献汇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版)第九十四册即据《遗真记》附录径题《古檀诗话》影印收录,实未及细察。
[10]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867页。
[11]王宏林《张宗柟<带经堂诗话>“附识”考论——兼论渔洋在乾隆诗坛的影响》,《纪念王渔洋诞辰38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16年版,第233—244页。
[12]郑幸《<随园诗话>的版本层次及其文献价值》,《中国诗学》第27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24页。
[13]黄裳《清代版刻一隅》(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221页。
[14]《清诗话全编•乾隆期》第一册,第275页。
[15]谢鸣盛《范金诗话》卷下,《清诗话全编•乾隆期》第八册,第4679页。
[16]吴镇《松花庵诗话》卷一,《清诗话全编•乾隆期》第六册,第3237页。
[17]如成书于道光元年的蔡家琬《陶门诗话》亦有“作诗必有我在,诗情始活”之论,见《清诗话全编•乾隆期》第十二册,第6828页。再如道光时盛大士《竹间诗话》卷三谓:“学明七子诗易落罾套。若诗中无我而专仗门面语,以为音节宏亮,则惑矣。或又多作感愤牢愁语,以为余法杜陵,则惑之甚者也!”则谓“诗中无我”。朱洪举、张宇超点校《清道光朝诗话六种》,吉林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15页。
[18]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22页。
[19]丁晏曾过录焦袁熹评语,辛德勇教授购得丁晏批本,并将其视为丁氏批语。参见辛德勇《丁晏批本<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读书与藏书之间》,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3—190页。[
20]周兴陆辑录数种《渔洋精华录》批点,其中最早的是乾隆二十年(1755)姜恭寿批本。焦本实早于姜本。见周兴陆编《渔洋精华录汇评》,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585页。
[21]郭兆麒《梅崖诗话》,《清诗话全编•乾隆期》第十一册,第6482页。
[22]石玲、王小舒、刘靖渊《清诗与传统——以山左与江南个案为例》,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549—550页。
[23]蒋寅《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6—287页。[24]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25][法]弗朗索瓦•多斯著,马胜利译《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Ⅴ—Ⅵ页。
【作者简介】张宇超,重庆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诗学。
原载《中国诗学》第3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下一篇:[图文当代最具收藏价值艺术家——刘典忠
注:本网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凡本网转载的文章、图片、音频、视频等文件资料,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

扫码关注
山东文艺网公众号

- 11-25小雪 彭连熙图说二十四节气
- 01-23在兰陵,该怎么说说这兰 ——
- 01-23兰陵兰/李立群
- 01-23兰茶雅会·文化之约/兰琪儿
- 01-23兰茶雅会 共赴文化之约
- 01-22怀念母亲/张守国
- 01-20参加了一个高端局
- 01-19兰茶一味/赵启民
- 01-19七绝·题兰贵人茶坊/丁士杰
- 01-19兰贵人茶业寄兴/朱虹